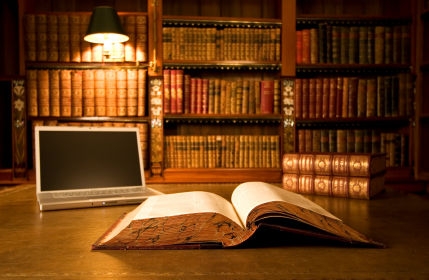导语: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没有怨恨,没有交恶。老人在回忆录中只有几笔记述,远不如快乐的事情多。他总结自己的人生:这一辈子,从记事起,国家和社会就一直在动荡,直到近年稍为安稳。能健康平静地活到晚年,是一种莫大的福分,有了这样的人生,只有欣慰,何来怨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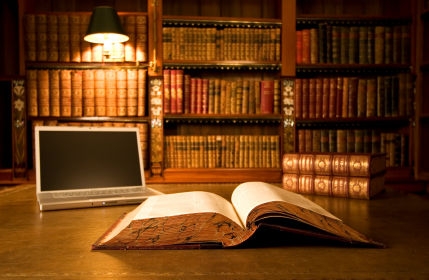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阿黛尔/文 79岁的退休老教授刘效曾最近很忙。每天除了雷打不动的两小时游泳外,其他时间几乎都花在电脑上:一部分是已经持续几年的中方与土库曼斯坦合作的石油勘探项目,另一部分,是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干了一辈子的石油勘探其实挺枯燥,倒是写回忆录让他兴趣盎然。
写回忆录是儿女的提议。亲家退休后写过一本六七万字的回忆录。说是回忆录,其实不过是整理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笔记,前面加点身世介绍,但家中亲人无不看得津津有味。儿女于是鼓励刘教授:爸,你的经历也很丰富,写出来会有意思。刘教授便应下来,反正他有几大本日记,写自己的事好像并不难。无非是时间顺序外加人物串联。
写回忆录无一例外地会讲到家族故事。好在刘教授刚刚帮长兄修订完家谱,并且印发给族中诸人。本来,家谱就是个“感恩体”外加“炫富帖”,又不是公开发表的历史学术著作,以厘清人物辈份为第一要义,虽然时常有错误之处被发现,但也无伤大雅。刘氏家谱“从明朝末年一位大官刘宗周,号念台,顺天府尹,原籍绍兴,为第一代开始记述延续下来”,非常有来历。祖上阔过,后人自然脸上有光。刘教授给同在修家谱的邻居看,邻居学问颇深,对他毫不客气:刘宗周明明是明末理学大儒,开创蕺山学派,连黄宗羲都是他的传人,结果让你们这些后人说成一位“大官”,太庸俗了。
刘教授如醍醐灌顶,这才明白祖先为何许人。于是隔三差五跑国家图书馆,翻《刘子全书》研究老祖宗。刘家迁京已经四代,绍兴早已无人。今年春天刘教授去杭州旅游,临时抽出一天专门奔到绍兴,希望能找到祖先的蛛丝马迹。按照家谱所说,刘家宗祠在解放大道,本想前去一探究竟,结果发现解放大道竟然六车道大马路,哪里有半点谁家宗祠的影子。虽然绍兴一日游无功而返,但刘教授还是很高兴,总算去过祖籍啦。刘家世代居此三百年,这最后一百年里,居然只有他一个男儿造访过此地,回忆录中,可添一笔。
每次查到与家谱有关的新资料,或者有了心得,刘教授都兴致勃勃地讲给家里人听。儿女不忍扫他的兴,也跟着听一些。倒是老伴儿烦他了:老祖宗都死了四百年,跟你有啥关系?
刘教授觉得当然有关系。刘家早已没落,但刘教授家9个兄弟姐妹,除了两个人参军,其余所有人都上了名牌大学。刘家是破落户,靠做铁路普通职员的父亲是养不活这么一大家人的,更供不上那么多孩子的学费。只能大的养小的,女儿养儿子——弟弟们去上清华,姐姐们去上北师大,学师范有奖学金,业余时间还能当家教。这难道不算源自祖籍的书香门第?
讲完家族历史,刘教授的个人记忆从小时在北平的生活写起,这段生活本不是他的重点记忆,无意中,子女向他推荐了北大哲学系教授何兆武的《上学记》。该书因记录了民国时期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实况而引起很大反响。何兆武的中小学在北师大附小和附中度过,是刘教授的师兄,与他的兄姐同学。刘教授将此书奉为至宝,读得既亲切又熟悉,认为此书弥补了他很多缺失的回忆。而且在写法上给他提供了很多思路,他不必将回忆录写得像流水账那样干巴巴,虽然家里人很喜欢看。
为了求证当年记忆,安家成都的老人家,每次来北京探望女儿,总要跟老同学老朋友聚会。这些七老八十的人,聚会得比年轻人还频繁。中间断了的联系,反而续上了。刘教授在中小学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后来官至高位,虽然他非常清廉平易,跟还是跟许多人断了往来,直到他退休赋闲之后,别人也爱避嫌。倒是因为很多回忆录里的内容,必须跟他求证,大家才又走动起来。结果发现,人,还是原来那个人,所谓官场生涯,在一些人身上是完全不留痕迹的。刘教授还有个要好的老同学,当初是香港左派,返回大陆支援建设差点被打成右派,刘当时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保了他。很多年后,这人成了大名鼎鼎的专家,念及旧情,在刘教授退休后,将他返聘至吐哈油田,做了大量勘探工作,两人在业务上堪称珠联璧合。这位同学的直系亲属,在当今港政府任高官,但当哥哥的他,依旧在北京过着朴素率性的生活。刘教授很喜欢他这些老同学,真诚,质朴,乐观,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却能获得冲淡平和的人生。
老人写回忆录除了要交待人生,免不了还念旧。特别是写到青春岁月,“情怀”就流露出来。刘教授在高一就考上了哈工大,并因为俄语水平突出,成为当时哈工大苏联专家团80多人的总顾问德良采夫教授的秘书。几年朝夕相处下来,自然深受影响。他至今爱读俄国小说,爱听俄国民歌,爱去莫斯科餐厅、基辅餐厅这样的地方吃饭。苏联专家撤走后,他也离开了哈工大,考进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就因为看了一部苏联电影《三勇士》,影片中地质队员在茫茫北极乘坐狗拉雪橇扬起风帆的形象触到了他内心浪漫的一面。这部电影影响了他一辈子,1958年,他随学院迁至成都,并读了整整四年半的研究生,留校担任教师。直到现在,他接手的土库曼斯坦项目一直全部用俄语进行。他对俄苏的感情,一点不亚于直接在那里留学的人。虽然在年轻时代,他从来没有到过俄国。当然,雪橇和风帆在他的工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那段自嘲的顺口溜倒是很形象:远看一群要饭的,近看一群逃难的,再一看是搞勘探的!
和普通理科出身的人要求子女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一样的是,刘教授一直喜欢自己的孩子学好文科,尤其是语文和外语。他受惠于自己流利的汉语和外语表达能力,除俄语外,还有英语。当年他参加教育部和地质部的统考,因为成绩异,1979年即被派往加拿大一年半,后来又去统一前的西德断续待了两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派出的访问学者之一。这也是回忆录中的重要内容。
当时,中国刚刚开放,极少有普通人能去到西方,共产党中国教授(他当时还不是,但当地报纸就是这么写)的到来常被当成当重大新闻事件来报道,当地华人和白人也纷纷邀请他们参加家庭晚宴,席间广泛交流各种思想,刘教授在回忆录中附上大量当时的日记,记录当时的访问学者所受到的特殊待遇,还特别提到,中国学者的业务水平未必比外国专家低,他们在德国,曾与指导专家就喀斯特地形发生观点分歧,最后事实证明中国专家正确,结果闹得德国专家很没面子,后来还对中国人耍了些小心眼。据他当时的看法是,北美的人普遍豁达洒脱,不拘小节,而欧洲人,真的是死要面子。
家人曾经与他探讨,第一次出国时,看到国外是那么发达先进,是不是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刘说,不算,因为林彪事件已经让很多人觉悟了。回忆录摘录了1971年11月1日的日记:“ 林彪问题今天公诸于世。刚听到时非常震惊,觉得天塌下来了。历史上,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毛的文革理论原先是自家炮制的,林彪事件将其粉碎,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这段日记记录了当时一个有着正常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结果。
老伴经常说他:你已经有那么多日记了,还写啥回忆录?查查日记不都明白了。但教授有教授的理论:日记哪有回忆录真实?日记记得太草率,好多事情只记了开头,后面怎么收的尾倒不记了。回忆录有逻辑,要把事情讲完整了,而且事隔多年,情绪退去,更接近事物的真相。
好多匪夷所思的趣事接着冒出来:一斤什么时候是从16两改成10两进制的?老大出生时是6斤多,为写回忆录查日记,原来是6斤14两,当时是60年代末,居然还是16两制?孩子到底是上午出生还是下午出生,查了日记,正式写进回忆录的是夜里1点出生,这样算出的八字才准。再比如,刘教授和老伴恋爱的最初介绍人到底是谁,这次也查明了,是两个人各自的同学共同撺掇的。他算自己和弟弟的生日:“我出生于公历1933年1月16日,阴历岁次壬申腊月廿一,,到了岁末腊月廿九晚上辞岁的时候,我这刚生下九天的娃娃就算两岁了。解放後改公元纪年,那时买不到万年历。别人给我算的生日是1月17日,身份证上也是错的。 述曾弟比我小一岁,生于1934年1月13日,岁次癸酉十一月廿八,属鸡。从阴历猛一看,他比我仅小11个月,但该年闰五月,所以还是小了12个月。此事在去年(2003年)10月四弟兄聚会时才说清楚。”这些,都是家族的痕迹,不足为外人道,却是人们探寻血脉根源的契机。
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没有怨恨,没有交恶。老人在回忆录中只有几笔记述,远不如快乐的事情多。他总结自己的人生:这一辈子,从记事起,国家和社会就一直在动荡,直到近年稍为安稳。能健康平静地活到晚年,是一种莫大的福分,有了这样的人生,只有欣慰,何来怨憎?
阿黛尔/文
79岁的退休老教授刘效曾最近很忙。每天除了雷打不动的两小时游泳外,其他时间几乎都花在电脑上:一部分是已经持续几年的中方与土库曼斯坦合作的石油勘探项目,另一部分,是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干了一辈子的石油勘探其实挺枯燥,倒是写回忆录让他兴趣盎然。
写回忆录是儿女的提议。亲家退休后写过一本六七万字的回忆录。说是回忆录,其实不过是整理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笔记,前面加点身世介绍,但家中亲人无不看得津津有味。儿女于是鼓励刘教授:爸,你的经历也很丰富,写出来会有意思。刘教授便应下来,反正他有几大本日记,写自己的事好像并不难。无非是时间顺序外加人物串联。
写回忆录无一例外地会讲到家族故事。好在刘教授刚刚帮长兄修订完家谱,并且印发给族中诸人。本来,家谱就是个“感恩体”外加“炫富帖”,又不是公开发表的历史学术著作,以厘清人物辈份为第一要义,虽然时常有错误之处被发现,但也无伤大雅。刘氏家谱“从明朝末年一位大官刘宗周,号念台,顺天府尹,原籍绍兴,为第一代开始记述延续下来”,非常有来历。祖上阔过,后人自然脸上有光。刘教授给同在修家谱的邻居看,邻居学问颇深,对他毫不客气:刘宗周明明是明末理学大儒,开创蕺山学派,连黄宗羲都是他的传人,结果让你们这些后人说成一位“大官”,太庸俗了。
刘教授如醍醐灌顶,这才明白祖先为何许人。于是隔三差五跑国家图书馆,翻《刘子全书》研究老祖宗。刘家迁京已经四代,绍兴早已无人。今年春天刘教授去杭州旅游,临时抽出一天专门奔到绍兴,希望能找到祖先的蛛丝马迹。按照家谱所说,刘家宗祠在解放大道,本想前去一探究竟,结果发现解放大道竟然六车道大马路,哪里有半点谁家宗祠的影子。虽然绍兴一日游无功而返,但刘教授还是很高兴,总算去过祖籍啦。刘家世代居此三百年,这最后一百年里,居然只有他一个男儿造访过此地,回忆录中,可添一笔。
每次查到与家谱有关的新资料,或者有了心得,刘教授都兴致勃勃地讲给家里人听。儿女不忍扫他的兴,也跟着听一些。倒是老伴儿烦他了:老祖宗都死了四百年,跟你有啥关系?
刘教授觉得当然有关系。刘家早已没落,但刘教授家9个兄弟姐妹,除了两个人参军,其余所有人都上了名牌大学。刘家是破落户,靠做铁路普通职员的父亲是养不活这么一大家人的,更供不上那么多孩子的学费。只能大的养小的,女儿养儿子——弟弟们去上清华,姐姐们去上北师大,学师范有奖学金,业余时间还能当家教。这难道不算源自祖籍的书香门第?
讲完家族历史,刘教授的个人记忆从小时在北平的生活写起,这段生活本不是他的重点记忆,无意中,子女向他推荐了北大哲学系教授何兆武的《上学记》。该书因记录了民国时期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实况而引起很大反响。何兆武的中小学在北师大附小和附中度过,是刘教授的师兄,与他的兄姐同学。刘教授将此书奉为至宝,读得既亲切又熟悉,认为此书弥补了他很多缺失的回忆。而且在写法上给他提供了很多思路,他不必将回忆录写得像流水账那样干巴巴,虽然家里人很喜欢看。
为了求证当年记忆,安家成都的老人家,每次来北京探望女儿,总要跟老同学老朋友聚会。这些七老八十的人,聚会得比年轻人还频繁。中间断了的联系,反而续上了。刘教授在中小学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后来官至高位,虽然他非常清廉平易,跟还是跟许多人断了往来,直到他退休赋闲之后,别人也爱避嫌。倒是因为很多回忆录里的内容,必须跟他求证,大家才又走动起来。结果发现,人,还是原来那个人,所谓官场生涯,在一些人身上是完全不留痕迹的。刘教授还有个要好的老同学,当初是香港左派,返回大陆支援建设差点被打成右派,刘当时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保了他。很多年后,这人成了大名鼎鼎的专家,念及旧情,在刘教授退休后,将他返聘至吐哈油田,做了大量勘探工作,两人在业务上堪称珠联璧合。这位同学的直系亲属,在当今港政府任高官,但当哥哥的他,依旧在北京过着朴素率性的生活。刘教授很喜欢他这些老同学,真诚,质朴,乐观,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却能获得冲淡平和的人生。
老人写回忆录除了要交待人生,免不了还念旧。特别是写到青春岁月,“情怀”就流露出来。刘教授在高一就考上了哈工大,并因为俄语水平突出,成为当时哈工大苏联专家团80多人的总顾问德良采夫教授的秘书。几年朝夕相处下来,自然深受影响。他至今爱读俄国小说,爱听俄国民歌,爱去莫斯科餐厅、基辅餐厅这样的地方吃饭。苏联专家撤走后,他也离开了哈工大,考进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就因为看了一部苏联电影《三勇士》,影片中地质队员在茫茫北极乘坐狗拉雪橇扬起风帆的形象触到了他内心浪漫的一面。这部电影影响了他一辈子,1958年,他随学院迁至成都,并读了整整四年半的研究生,留校担任教师。直到现在,他接手的土库曼斯坦项目一直全部用俄语进行。他对俄苏的感情,一点不亚于直接在那里留学的人。虽然在年轻时代,他从来没有到过俄国。当然,雪橇和风帆在他的工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那段自嘲的顺口溜倒是很形象:远看一群要饭的,近看一群逃难的,再一看是搞勘探的!
和普通理科出身的人要求子女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一样的是,刘教授一直喜欢自己的孩子学好文科,尤其是语文和外语。他受惠于自己流利的汉语和外语表达能力,除俄语外,还有英语。当年他参加教育部和地质部的统考,因为成绩异,1979年即被派往加拿大一年半,后来又去统一前的西德断续待了两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派出的访问学者之一。这也是回忆录中的重要内容。
当时,中国刚刚开放,极少有普通人能去到西方,共产党中国教授(他当时还不是,但当地报纸就是这么写)的到来常被当成当重大新闻事件来报道,当地华人和白人也纷纷邀请他们参加家庭晚宴,席间广泛交流各种思想,刘教授在回忆录中附上大量当时的日记,记录当时的访问学者所受到的特殊待遇,还特别提到,中国学者的业务水平未必比外国专家低,他们在德国,曾与指导专家就喀斯特地形发生观点分歧,最后事实证明中国专家正确,结果闹得德国专家很没面子,后来还对中国人耍了些小心眼。据他当时的看法是,北美的人普遍豁达洒脱,不拘小节,而欧洲人,真的是死要面子。
家人曾经与他探讨,第一次出国时,看到国外是那么发达先进,是不是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刘说,不算,因为林彪事件已经让很多人觉悟了。回忆录摘录了1971年11月1日的日记:“ 林彪问题今天公诸于世。刚听到时非常震惊,觉得天塌下来了。历史上,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毛的文革理论原先是自家炮制的,林彪事件将其粉碎,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这段日记记录了当时一个有着正常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结果。
老伴经常说他:你已经有那么多日记了,还写啥回忆录?查查日记不都明白了。但教授有教授的理论:日记哪有回忆录真实?日记记得太草率,好多事情只记了开头,后面怎么收的尾倒不记了。回忆录有逻辑,要把事情讲完整了,而且事隔多年,情绪退去,更接近事物的真相。
好多匪夷所思的趣事接着冒出来:一斤什么时候是从16两改成10两进制的?老大出生时是6斤多,为写回忆录查日记,原来是6斤14两,当时是60年代末,居然还是16两制?孩子到底是上午出生还是下午出生,查了日记,正式写进回忆录的是夜里1点出生,这样算出的八字才准。再比如,刘教授和老伴恋爱的最初介绍人到底是谁,这次也查明了,是两个人各自的同学共同撺掇的。他算自己和弟弟的生日:“我出生于公历1933年1月16日,阴历岁次壬申腊月廿一,,到了岁末腊月廿九晚上辞岁的时候,我这刚生下九天的娃娃就算两岁了。解放後改公元纪年,那时买不到万年历。别人给我算的生日是1月17日,身份证上也是错的。 述曾弟比我小一岁,生于1934年1月13日,岁次癸酉十一月廿八,属鸡。从阴历猛一看,他比我仅小11个月,但该年闰五月,所以还是小了12个月。此事在去年(2003年)10月四弟兄聚会时才说清楚。”这些,都是家族的痕迹,不足为外人道,却是人们探寻血脉根源的契机。
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没有怨恨,没有交恶。老人在回忆录中只有几笔记述,远不如快乐的事情多。他总结自己的人生:这一辈子,从记事起,国家和社会就一直在动荡,直到近年稍为安稳。能健康平静地活到晚年,是一种莫大的福分,有了这样的人生,只有欣慰,何来怨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