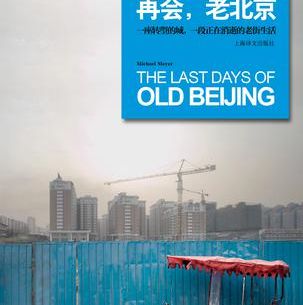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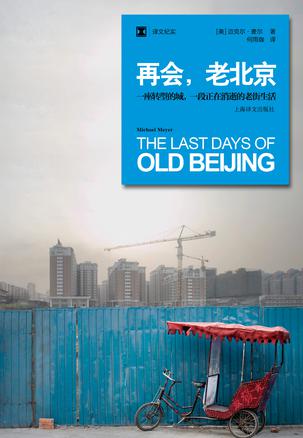
《再会,老北京》
作者:【美】迈克尔·梅尔
译者:何雨珈
上海译文出版社
by 湛眉
北京对胡同的洗劫早已开始,从未止步。这种在过去构成老北京元气的社区形式在如今被视为贫穷和落后的象征,拆迁以外的时间里,它们默默生长,乏人问津。而除了一些供外地游客参观的“模范街道”,似乎其他的一切都亟待被改造和重建,又假如背后有足够的经济利益驱动,那么仅存的样板街 道,也不再能成为例外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胡同嗤之以鼻,无论是胡同外的,还是胡同里的,虽然老人们执着地渴望“接地气”,但年轻人往往愿意搬到更宽敞和时尚的高楼里。“无形的巨手”会在某一天给胡同的墙上画上一个大大的“拆”字,之后有人欢喜有人忧,这最终取决于拿到手的补偿款是否令人 满意,虽然结果往往是令人失望的,但被无形巨手点到的人,只能在一番挣扎后屈服。胡同的衰败和没落势不可挡,但不是所有人都对其视而不见。当全世界都在争论城市需要什么样的社区时,合适的人口密度,友好的邻里关系,丰富的功能区,以及更低的犯罪率都是被首先考量的指标。这时,在北京的老胡同里生活了3年, 并写出了一本《再会,老北京》的美国作家梅英东(Michael Meyer)说:这些东西,胡同早就已经实现了。
没有牙的吸血鬼
迈克尔·麦尔,中文名梅英东,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做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虽然也经历过正统的学院教育,但迈克尔的中文主要还是学自市井,一个人的口音常常是他所停驻的地方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记。迈克尔的中文非常流利,沾染了京腔,儿化音蹦来蹦去,日常会话从无障碍,很多学究气的词汇却并不通晓,这是因为他从来到中国之初,亲近的就是最平常的生活,这种性格由来已久,即使是做记者时,迈克尔也不喜欢打打电话,聊一两个小时天的采访方式,在他看来,那就像在吸血,“上前咬一口,吸了血就飞走了,没有下文”,他更乐意坐在胡同的街边,和人们一起生活,随意地聊天,去体验和长期地关注,“我要做一个没有牙齿的吸血鬼,”这是迈克尔的执着。
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的迈克尔,最深切地体会着城市变迁给人带来的去家乡化,那个一度生养自己的地方,再回去时,却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熟悉,这是所有家乡被改造了人们的共鸣。从美国到中国,从四川到北京,所有城市都像是走在高速公路上,城市建设愈演愈烈,又毫无章法,人们摸不准它的方向,更跟不上它的速度,于是处处皆是异乡。但北京是个令他一见钟情的城市,他在九十年代末移居北京,那时的大拆大建尚未直入眼底,他嗅着这个城市里的人情味儿,觉得找到了第二故乡。正因为如此喜爱, 当看到这个城市也在变得越发陌生的时候,他决定把老北京最后的日子记录下来,这本《再会,老北京》的英文版原名为: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老北京 最后的日子: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也正如他毫不掩饰的野心所透露出的,这是一本写给母亲的书,也是一本一百年后的读者用来追忆老北京的书。
写一本立足当下的书并不难,但在这个碎片满天飞的时代,笃信自己的书在一百年后仍保有价值,却着实不易。迈克尔最喜欢的作者里面,有狄更斯,有海明威,有老舍,他喜欢看老伦敦的故事,也喜欢听老北京的讲述,正如他亦坚信自己所记录下的故事,可以帮助一百年后的读者,去想象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迈克尔眼里,故宫、天坛、中南海,这些没有人生活的地方是死的遗产,只有像大栅栏一样,有人每天生活在里面的,才是活的遗产。《再会,老北京》是活化的历史和细节的生活,故事与历史连成一个完整的环,看似并无章法可循,却又环环相扣,将故事结构的骨架埋藏于具体描述的血肉之中,才构成了本书真正的可读性,这是非虚构作品中,中国作者写中国所从未做到的。但当问及迈克尔,这位如今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并获得过多个写作奖项的作家,却坦言,“我只是将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和有意思的故事记录下来。”所谓写作的技巧,早已融汇于他的血液和本能之中,一切我们所以为是刻意的雕琢,最后都只能被证明为一派天然。
胡同是个大熔炉
在北京生活多年,迈克尔早已对这里的历史如数家珍,他对这里的了解,也早已超过了对自己故乡的认知。迈克尔喜欢大栅栏,清军入关时,被赶出皇城外的许多汉人就是迁居于此。与皇城内的棋盘式结构不同,这里没有严格的规划,手工艺人和商人 在这里生活,才重新建构了大栅栏的格局。而如今的大栅栏,在迈克尔眼里成了一个大熔炉,是这个大熔炉,让外地人渐渐变成本地人,一条条胡同为外来务工者提 供了灵活的工作机会和相对低廉的居所,他们开始说北京话,在北京纳税,也希望将孩子接来北京读书。胡同给了每个人自己的角色,这是其他城市内的社区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迈克尔曾试图以一个胡同里的居住者的身份与城市的规划者交谈,他不断重申,美国在五六十年代也曾为了建造公路而大量拆掉老城镇,可更多的路只是引来更多的车流,居民的生活也只是变得更加不便,中国不该走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道路。但很多人的回答都让人心凉,“我们想犯美国犯过的 错误,我们现在有权力,更有能力这么做!”可悲的是,无数个大城市也都走上了这个循环,推土机却仍保持着巨大的惯性,人们总是固执地认为,新的就是好的, 那些已经和即将被拆掉的东西,仅仅是城市的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新陈代谢,却往往忘记了,城市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建筑,一切打着追求经济利益旗号的践踏和破坏都 终将是一场骗局。
迈克尔所记录的四合院生活里,有整日忙碌却收入微薄的“废品王”;有一心想把儿子接来北京未果的韩先生夫妇;有勤勤恳恳经营着一家美味面馆,最后却被拆迁的刘老兵……这样一副平平常常的众生相发生在城市的许多个角落,高楼大厦和其他住宅小区所体会不到的人情味儿在这里喷薄而出,但错误的城市规划和所谓的保护性拆迁,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之摧毁殆尽。
无形的巨手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形巨手’会在 我所居住的胡同院墙上画上一个‘拆’字。但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不奇怪,实际上很多胡同都是这样消失了。”这双无形巨手是《再会,老北京》中唯一的反面角色, 它让人联想起《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和奥威尔一样,迈克尔并没有写清无形巨手是什么,它又属于谁。他一直提到它,却保持着冷静的克制,不去激怒它, 同时也不被这双巨手所激怒。“一个作家需要去寻找一个反面人物,在写作之初,我就祈祷能够早些早找它,然而最后它都没有出现,这双无形巨手没有一个具体的 形象,无法站出来,而我随即意识到,没有人知道它是谁,这才是北京最大的问题。”
因为无法和这双无形的巨手去直接地发生关系,迈克尔决定在写作中不做出任何带有偏见的判断,只是做个客观的记录者。他的眼睛就是一台摄影机的镜头,去观察,而不让自己过多的出现在作品里。这同时也是迈克尔作为一 名非虚构作家,与何伟(Peter Hessler)不同的地方。他们两人虽然同为和平队的成员,是好友(何伟甚至说过,迈克尔是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人之 一),然而却经常因为写作上的问题发生争论。不过所有非虚构作家都认同的一点是,真实性要高于故事性,当故事的发展脱离了设想的轨道,也只能让真实延续下 去。
迈克尔笔下的主角之一,是他所居住的小院的“房东”老寡妇,只是像她这样的所谓房东,其实并没有房子的所有权。老寡妇是这个小院儿的灵魂人物,是老北京人情味的化身。这个小小的胡同一直被不知何时会开始的拆迁所威胁,老寡妇不断地告诉迈克尔,“小梅,我不会离开这儿,不会。”但在拆迁开 始之前,老寡妇就“明智”地搬走了。失去了老寡妇的小院儿不再让迈克尔熟悉,老寡妇长抽的飞马牌香烟的味道在这里彻底绝迹,伴随而去的还有那句老寡妇挂在嘴边但从未履行的“公是公,私是私。”迈克尔不需要等到拆迁作为这本书的结局了,老寡妇的离开,让一切回到原点,他又一次失去了故乡。
在一次讲座上,迈克尔问读者:你的故乡在哪?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