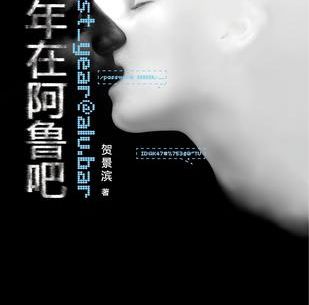

《去年在阿鲁吧》
贺景滨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btr/文
在台湾文坛,贺景滨是个异类,也是传奇。早在1990年,贺景滨就凭《速度的故事》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当年的评审张大春 说,“《速度的故事》及其获奖的评审过程实则凸显了小说界对于形式自由的巨大渴望,即使它们无法唐突也不可能崩坏一个具有长久历史的小说传统。值得庆幸的 是:贺景滨只能运用此一极端的嘲谑来处决小说一次而已,在充分获得书写或想像的自由之后,叙述传统将获得再生的机会。”
十五年后,一个偶然 的机缘导致了《去年在阿鲁吧》的诞生。当时贺景滨带着孩子在路边吃面,在报纸上看见了“林荣三文学奖”小说征文的消息,于是便写了《去年在阿鲁吧》的第一 章拿去参赛,结果又一次获奖。虽然写作中途他罹患癌症,但他仍凭坚强的意志完成全书,并从癌症中康复过来。“《速度的故事》是向现代主义道别的作品,”贺 景滨说,“到了《去年在阿鲁吧》,则是想厘清自己身上那些后现代的东西。”
作为2013年上海书展暨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嘉宾,贺景滨来到了新 近开幕的“思南公馆文学之家”,与广大读者分享《去年在阿鲁吧》的创作过程及关于写作的种种思考。他自陈,写小说经常是为了探寻一个问题,而《去年在阿鲁 吧》试图用文学的思维来探讨科学,来理解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在“思南公馆文学之家”贵宾室里,贺景滨先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问=经济观察报
答=贺景滨
问:小说里出现了很多三个英文字母构成的缩写词。你对众多人物和事物进行了定义或重命名,就好像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答: 我发现国内外有这个趋势,中文叫“拼合字”,但因为英文与中文构成不同,无法写成一种“会意字”。在一个愈来愈复杂的社会里,缩写词越来越多,你在一本杂 志里就能找到很多。于是我想借用这个概念来达到一种“未来化”的效果,并藉此创造一个陌生的世界——那个世界有自己的命名法则。
问:你的小说涉及了数学、哲学、量子物理学、生物学甚至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为什么要在小说里使用如此多的理论学说?
答: 在科学唯物主义横扫世界的时候,如果放弃科学,就等于放弃了和它对话的机会。有个宗教大师说,即使是宗教领袖,也需要去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曾 说,面对实证证据的威信,如果去拒绝它,就会丧失参与重要对谈的机会。所以,文学如果放弃科学,就等于放弃与之平起平坐的机会了。我在书中也写了:这个时 代如果不谈科学,就和在维多利亚时代不谈论性一样虚伪——因为那是你每天要面对的东西,你用微波炉的时候,就已经在面对量子物理了。
问:说到“虚拟实境”,小说探讨了真与假,信与不信。而宗教常常也是某一种“信”。你是一个有宗教感的人?
答: 在我看来,信仰是基于恐惧产生的想像。没有恐惧,就不可能有宗教。在中国,古时人们说宗教就是“畏天”,敬畏或害怕某种东西。从起源看,在原始时代,人们 在丛林生活,看见远处有个黑影,就会害怕而离开;而常常是这种恐惧,让人活了下来。慢慢地,害怕某种你所不了解的东西,便成了信仰。在小说的虚拟世界里是 一样的,就看大脑会害怕吗?所以科学再怎样发达,都无法去除信仰,因为恐惧始终存在。
问:《去年在阿鲁吧》在叙事上很有意思:虽然一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但到了两人互换身体那一章时,连“我”是谁也变得不再确定了。你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叙事视角?
答: 其实在人称的运用上,我自己也蛮自豪的。(笑)只用第一人称,就能写出不一样的“我”,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我还在想,在下一部作品里,要怎样打破人称这 个东西,因为叙事最主要的就是人称,你一下笔就需要决定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在我看来,第二人称只是第一或第三人称的变形。村上春树曾说,对他来说, 第一人称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宿命”。对于所有的小说家,人称都决定了基调和格局。
问:《去年在阿鲁吧》叙事的语气是非常放松的,甚至带有一些戏谑的意思;而小说本身却又是非常严肃的。你如何看待这种叙事的语气?
答: 首先,艺术是需要平衡的。当你想要写“冷”的时候,你需要“热”来平衡。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个冷的故事,所以我想把它写得热情一点。如果一直冷到底,可能会 让人看不下去,变得孤僻,变得艰涩难懂。第二,好的文学通常都是“嘲讽”的——这也是小说最珍贵的地方。因为人都是会为下一步而作准备的,而小说的智慧常 常在下两步——即对下一步的颠覆、扭转、反转。我并不只是在讲科学,而是把科学拿来,用嘲讽来谈。所以我不是被科学牵着走,而是要用文学来和科学对话。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