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迈克尔·斯坦福
英国历史学家,曾获历史与哲学双学位,长期执教于西英格兰大学,至1983年退休。退休后致力于撰述史学著作,先后出版了《历史知识的本质》、《历史研究导论》、《历史哲学绪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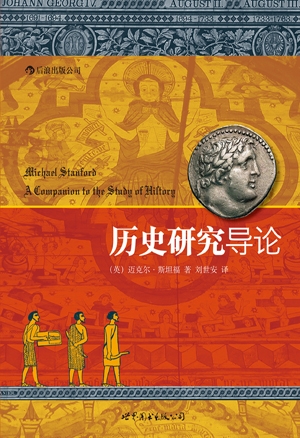
1989年,中欧及东欧诸国纷纷摆脱苏联的桎梏,宣布改建为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西方世界欢腾不已,其中有一位是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如同一般典型美国公民一样,认为自由、民主就是进步的终点,因而提出一声名远扬的结论,声称此即“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已无更多变革可以期待。据报道,许多中学生曾殷切追问,历史的终结是否也意味着代数的终结。
这则故事表明了本书将和读者探讨的若干要点,例如历史关心变革,历史进程可视为走向佳境的演进,历史活动多坐落于政治场景之中,历史既关系到往昔,也关系到现时。然而最紧要的,它彰显出“历史”一词的含混性。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务必铭记作为事件的历史(history as event)与作为记述的历史(history as account)之间的重要区别。1989年,东德人民曾有若干行动,包括拆毁柏林墙。这些事迹(deeds)不仅见诸报端、电视,更有政论家如福山等加以讨论。随后,这些事迹必然载入史册。先有行动,继而有图像、口头或书面描述。根据我的叙述,对拆毁围墙一事,读者脑海中便留下了大致清晰的印象,但却不可能详细的了解此事的细节。 “历史”一词,既可指世间曾经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也可指通过文字或理念将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基本连贯的记述,二者混淆不清也在所难免。然而二者的区别却非常明显。为了区分,若干学者采用作为事件之历史[history(e),简称历史事件]、作为记述之历史[history(n),简称历史叙述]加以区别,其中(e)代表事件(event),(n)代表叙事(narrative)。其他学者则以甲类历史[history(1),简称历史(甲) ]、乙类历史[history(2),简称历史(乙)]为之区分,甲或乙表明其究竟属于一级或次级事实。本书在必要之处采用后一种区分。
吉本(Gibbon)评论说,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与许多人一样,笔者总以为一生过短,不够鉴赏所有历史学家笔下早先存活于世之男男女女。然而传颂先人者又岂止历史学家而已,大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名诗《序曲》(The Prelude),就是一名青年在1790年7月(巴士底狱失陷一周年)前往法国时的所见:
一人的欢愉就是千万人的欢愉时
他所显现的容颜又是何等的光辉
稍后则
漫步在幽僻乡间
只见仁爱幸福四溢
犹如芳香,犹如春天
后续诗句紧接着描绘当时的宴乐、欢舞。若能亲身前往分享他们的快乐,尤其是分享他们的希望,岂不快哉。
撇去这种特殊场景,在笔者的想象(imagination)中,始终留有17岁时阅读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一书时曾经获得的印象。人在读史时,常有一种倾向,好将恺撒、克伦威尔、林肯视为小说中的英雄、女英雄。但威尔斯塑造的英雄却是“人”,所有叙述完全围绕在这个饶有趣味的角色上。从此以后,笔者心中除了各种专门历史外,总有一部凌驾于其余历史之上的历史,它始自旧石器时代猎人塑造女性小雕像、在洞穴墙壁上涂画野兽,绵延至今日的你我,并且将绵延至你我的儿辈、孙辈……我们既有如此绵长系列的先世,又有如此众多的同辈,还能遥望聪慧、幸福将甚于你我的无数后裔。历史予人以一个大家族的感觉。
上述思想着实鼓舞人心,然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随之而来,即我们对整个人类大家族所知何其少。关于它的历史,显然绝大部分不为我们所知。当然,若是即使我们知道得更多,却不太可能很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观念,那么所知甚微也就无关紧要了。另一方面,正像某人抛妻弃子使我们视如恶徒,然而日后,我们在对其妻儿认识较多后,或许足以了解他何以如此,也就可能以更宽恕之心看待他。因此,凡是人们相信的历史,都有修正的可能,因为关于历史,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即我们所知甚微。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对往昔并无直接认识,所知也就极为有限。凡人们自称的认识,概属间接认识。也就是说,人只能就当时可得的直接认识,例如从所谓的证据之中,推理出可信事物。犹如在森林中漫步的孩童,由于不曾听到、也不曾看见,所以无法断定眼前洞穴之中是否有熊。可是却因为发现地面留有大型爪痕一路向洞穴延伸,却不见有离开洞穴而去往他处的爪痕,所以相信洞中有熊。这种推想可能正确,然而我们也能举出若干设想,足以说明孩童的推想有误,比方说熊可能已由洞穴后面出口去往他处,可能爬上山石去往他处,因此不曾留下爪痕,或者这些爪痕根本出于他人的恶作剧。孩童认为洞中有熊,乃是就证据间接推想而得,除非大胆入洞一探究竟,而且还真的撞见熊,否则就无法确知洞中是否有熊。历史与此类似,只是我们永远无法进入这个洞穴。
若如以上所言,为何笔者又撰写本书?笔者用意乃是要显示,若能给予恰当认知,历史对所有人都十分重要。同时,我还要更进一步说明如何方能恰当认知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