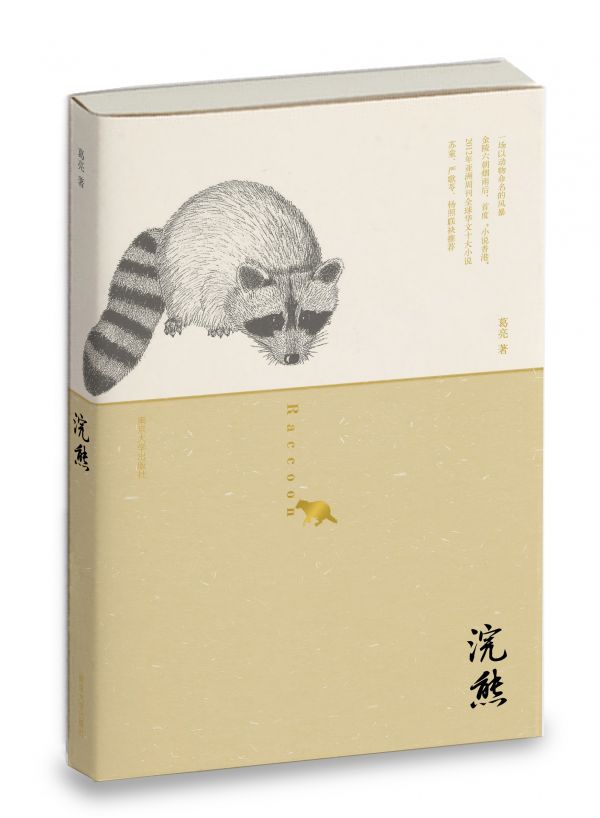
《浣熊》
作者:葛亮
南京大学出版社
葛亮:对,似散又似聚。因为我们都把这263座岛屿统称为香港,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仅仅是九龙、港岛。甚至另外一座大型的岛屿大屿山,除了搭飞机或者去迪士尼都很少去到。所以说,可以讲我最初对离岛的看法,我也感觉到它的空间真的就是刚才说的一个词“不期而遇”,原来香港还有这样的地方。仅仅一座长洲,它分东边和西边,你会觉得它体现出来的是不同城市的格局。这么小的地方,是体现一个具体而微不同城市的格局,有古老的关帝庙,还有所谓的现代化的泳滩,也有五星级饭店。
而且这座岛屿保留了香港了一些最为原始和传统的节庆,比方说太平清醮。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香港是一个不缺乏历史的城市。而且也是一个致力在保留某些历史讯息的城市。这一点甚至比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城市,大型城市的状况要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香港的意义,就在于,因为我们一直说香港是一个杂种城市,陈冠中老师也讲过,这是香港非常重要的特点。而它的意义就在于,在所谓交杂之间,有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当年王韬1874年到香港以后,他把香港称为蕞尔小岛,一个蛮荒的地方,它实际上是独立中国大陆之外的,而所谓的宗主国英国对它进行长达百年的殖民。其实它跟英国本国之间存在非常遥远的距离。它如何凸现自己作为城市鲜明的文化气质。我自己的感觉,恰恰在交杂性的中间,在不断碰撞过程中间,它有一种自发向上的部分。
主持人:从葛亮的叙述我们发现,他对香港的关照是非常的细腻。之前看葛亮的《朱雀》是历经五年的力作, 我们发现其实如果大家对南京这座城市有兴趣的话,不妨把葛亮的《朱雀》当一个文化导游书。他的《浣熊》,我发现也可以当香港的文化指南来看。《浣熊》这本小说是当下的香港, 你可以看到香港发生的事件,中环、油尖旺、天水围是大家很熟悉的文化名词,而不只是地点了。 每一个地点都是我们身边很熟悉,就是不同的不期而遇。我希望大家看的时候,会碰撞出各自不期而遇的火花。就像两天前葛亮打电话说,有这么一个讲座,来帮忙听听故事。那时候我在北京,感觉好像南北之间的一个电话线给我们联在一块,我有机会给大家讲故事。我又想到南北不同的城市,我在北京的时候,突然收到南方的一个电话,感觉既遥远又亲切,在葛亮这部小说里,我正好看见他收了一篇和苏童老师的对谈,里面就是关于南北的对谈。 我们一起听葛亮讲讲,好吗?
葛亮:跟苏老师对谈当时是有一个语境的,就是当时广州南方文化周,围绕于此是想让我们谈一谈,这个对谈的主题叫“文学中的南方”,因为苏童老师现在长期生活在南京,而祖籍是苏州,是很地道的南方人,江南人。所以当时我们的对谈是基于两个南方人如何两看待中国所谓“南国”所指代的文化意向。中间就谈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昨天我还聊到,就是有关于在文学表达中间时常浮现的,所谓的大中原心态。
主持人:大中原心态?
葛亮:因为当时苏童老师和我都讲到一点。我们在进行文化审视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词叫“北望”,但是很少讲“南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政权实际上多建立在北方。所以南方的文化从某种意义来说,在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过程中间,它不是一种强权,不是一种占优势的文化态势,无论是岭粤文化也好,还是江南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如此。作为一个南方作家,当苏老师讲到很有趣的一点 。我们谈到一个话题, 你会用方言写作吗?
主持人:葛亮作了很大胆的尝试,在《浣熊》里面就用了很多在地化的语言。
葛亮:应该这么说, 我们当时探讨的话题,就是是否可以用南方的语言,纯然用南方的语言写小说。当时苏童老师举到一个例子是《何典》,我当时举一个例子是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你知道《海上花列传》完全以吴语来写的,就是因为完全用吴语来写,影响了它的传播。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适当在小说当中运用方言是值得尝试的一件事情。
你在写作的过程中间,运用方言我觉得实际上是有没有“度”的一个问题。适当方言的使用,会使你的作品里凸现出来一种有关于地方的鲜活感。换而言之就是实际上有时候运用方言是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去表达你小说中设置在地化的语境。甚至有一些东西,比方说 广东话里有很多的词汇,如果你把它特意变成标准化的现代汉语,实际上很多东西就剥落了。包括中间的一些粗口,我也有写到过。比方说广东话有一个常用的粗口“黐线”,对应的普通话是说“神经病”,你会对它的感觉一下子薄弱了好多,虚弱了好多。这种方言的使用是有一个“度”在里面。南方文化的部分,我觉得它的鲜活感就拿广东文化来讲,我觉得这种鲜活感最重要是体现在他的语言系统,它和标准汉语白话的语言系统,实际上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当时苏童老师也讲到,就是说有一些方言实际上跟普通话,或者跟现代汉语的叠合,使得彼此之间沟通不受影响。而他看了一些广东或者是香港非常在地化的报纸,就是完全以粤语书写系统来写的,来进行表达的报纸,会觉得看不懂,就像外语一样。所以对粤语,当我在这个小说里面涉及对粤语的表达,对在地化语言因素的选取,实际上是要抱有一种审慎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小说仍然有很多的机会和在粤语方言系统之外一些朋友,一些读者在分享。你要把你在小说里面方言的使用定位到相对比较精准的一个尺度。运用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它的意义在于表达特定的语境,还是是把它用于语言的工具,这是有区别的。我更多是把它定位在前者。
